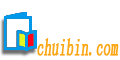教育民族志方法的探讨
教育民族志方法的探讨
樊秀丽
摘 要:研究者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运用到教育研究中,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直接、便捷和真实地反映研究者的研究路径和在与被研究者互动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完成定向理论分析,这一过程称教育民族志。教育民族志是一种整体性的描述,这种方法的运用可以拓宽对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丰富研究内容,特别是对于挖掘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的许多不可视的和不可量化的因素有独特的贡献。近年学者们在教育领域中运用这一方法时出现了一些概念的混淆、误解和误用,因此本文旨在探讨这种研究方法的来源、概念、原理及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使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不断地得到完善和丰富。
关键词:教育民族志;田野调查法;教育实证研究;整体性
一、引言
研究者把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运用到教育领域,从宏观到微观以及现实等角度,描述和解释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解决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民族志”方法在教育领域中运用被称为“教育民族志”。教育民族志方法要求研究者从研究内容本身和课题性质的需要出发,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在实际场域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向理论分析。这种方法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根据现场情况来把握研究进度,并配合适当的文献分析。
教育民族志是一个研究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是研究成果的表达之一,它的运用可拓宽对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丰富研究内容,特别是对于挖掘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的许多不可视的和不可量化的因素(诸如人的情感、人文环境等)有独特的贡献。教育民族志通过整体性地描述,直接、便捷和真实的反映研究者的研究路径和与被研究者互动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并根据长期的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与理论研究,撰写民族志。这对于被研究者来说是将他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具体化、细致化。从而促使没有进到该研究场域的研究者及“身在其中之人”可就已形成的“教育民族志”进行反思或者进一步地研究,可以说,教育民族志使教育研究者更加贴近他们的研究对象,更加清晰地去明了什么问题真正存在?什么问题亟需解决?什么是教师或者学生最关注的?
近年来学者们将民族志方法运用在教育研究中,然而却出现了一些概念的混淆、误解和误用。比如.对“ethnography”的误译和对其概念误解。另外还将民族志方法错误地与“质的研究”或“教育实证研究”等等同起来,各种方法没有确切的区分。就教育民族志方法来说,是从人类学领域中发展起来,它不同于被称为“自然调查法”、“个案调查法”、‘现象学的方法”等研究方法,而有其自己的一套严格的田野调查的规范性要求。本文将首先澄清“ethnography”的概念,并对上述的一些方法的误用和误解等问题进行分析。
二、教育民族志
(一)澄清“ethnography”的概念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ethnography”这一概念。笔者在参加评阅学生的学位论文以及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些论文中发现,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常用“人种志”(ethnography)这一词来描述使用参与观察。比如:《人种志方法与课堂研究》(2002)、《人种志研究与教师智慧的生成》(2006)、《基于人种志视角的课堂观察理论与实践》(2007)、《论人种志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优势》(2007)等近数百篇的论文都出现“人种志”这一用语,可见如此之多的教育领域中的学者对“ethnography”一词并未真正理解。
“ethnography”一词的含义是对特定民族和群体的文化、社会做出具体和准确的描述与解释。将ethnography翻译为“人种志”,这是一种误译,应译为“民族志”。“人种(race)”是生物学的用语,是对地球上现存的人类用先天的、遗传的身体上的特征(尤其是皮肤、毛发、眼睛的颜色、身高等外表具有明显的特征)进行分类时的基本标准。比如:我们通常将地球上的人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人”等等。“ethnography”一词中的词根“ethno”源自希腊语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表示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方式、归属于同一集团意识的人。“graphy”作为“志”是对一个民族和群体的描述,二者合一译为“民族志”更为准确。皮科克(Peacock)对“民族志”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民族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细的、动态的、情境化的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二)教育民族志的内涵
民族志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人类学特有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运用于研究教育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则产生了“教育民族志”。其核心是“田野调查”。“教育民族志”就它自身的属性来说。是一种以参与观察和整体性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它属于教育人类学的方法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艾迪(Eddy,E)、奇尔科特(Chilcott,J.)、米德(Mead.M.)、斯宾德勒(Spindler,G.D.)等人开始把民族志方法运用到以学校为单位的研究中,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教育民族志”、“教育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教育研究的民族志技术”等。此后美国学界大力提倡教育研究领域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在这之中,威尔逊(Wilson,s.)和勒孔特(LeCompte,M.D.)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1977年,威尔逊发表了《教育研究中民族志技术的应用》(The use of Ethnographic Technique in Educational Research)一文.文中威尔逊系统阐述了民族志方法论对教育研究可能做出的贡献。这篇学术论文在教育人类学研究领域引起较大反响。随后1978年,勒孔特发表了《学会田野调查:课堂中的隐性课程》(Learning to Work: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the Classroom)一文,采用民族志方法,试图从微观研究的角度建立学校和班级生活研究新的领域”。
“田野调查”作为教育民族志的核心,是指研究者长期深入到某一社区或某一群体。同当地人们一起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各项活动,通过参与观察、访谈、体验等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方法。其中“参与观察”和‘访谈”是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它通过田野调查,使研究者获取某一群体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提炼出观察研究的精华、撰写民族志,继而完成定向理论证明。这三个研究步骤的结合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提出完善的,至今被认为是人类学研究的典范。
除上述特征外,田野调查更强调研究者没有预设立场,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先入之见在任何学科中都是有害的。但预拟问题却是科学思考者的主要禀赋,这些问题是通过观察者的理论学习发现的”。[8]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不要用自身的价值观去衡量当地人。
从整体上讲,田野调查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每位研究者根据所研究的问题选择独立的研究环境,并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者会选择不同的研究计划和不同的研究方法。
在教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一般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宏观和微观层次上。威尔科克斯(Wilcox.K.A)在《论作为方法论的民族志及其在学校教育研究中的应用》(Ethnography as a method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schooling)(1982)一文中提出,宏观层次适用于大的单位和环境,它可以用集中研究整个社区、学校等。微观层次适用于小的单位和环境,如一个班级、学生群体、学校教员与行政人员等。通过民族志方法,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形成互动关系,而真正观察到学校中究竟发生了什么。[9]下面就教育民族志方法与其他教育研究中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进行探讨。
三、教育民族志方法与教育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教育民族志方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不是一次性的、终结性的研究,而是在得到初步探索性资料后,寻找问题、界定、再次调整研究计划,再次进入研究场域。这一研究过程是具有循环性的,这便使民族志研究更加灵活,并成为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别的一个特征。与研究者在资料搜集过程中保持原有研究设计不变的教育实证研究的线性的研究相比.民族志研究中的循环过程可以描述即时即地反复发生的事件,并适时调整研究计划。根据需要重复这一过程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问题,得出整体的解释。因此,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必须与被观察的对象之间进行连续的对话,而理论就来自于这种对话的过程。民族志研究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促进理论的发展,[10]而理论又来源于循环的研究过程。
一般教育实证研究是以界定问题→建立假设→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分析资料→成果呈现这一研究过程。而这一研究的过程首先从时间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上是受限的,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二元”关系,即从研究一开始,研究者就带着自己的预设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了相对的关系,从而研究大多是一次性的。[11]比如问卷的设计,也并非是经过参与观察之后设计的。在此举一问卷的例子来看,在费城,有一份由训练与背景都合格的人所拟的问卷。问卷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家长对社区关系政策与人员的看法。该问卷如期施测。施测的研究生又通过非正式与家长交谈,发现他们对问题的诠释不同于原设计者与学校。他们区分运动场(有专门设计供学生使用者)与操场,但是问卷上却二者不分。当询问他们是否有机会与学校/社区联络人员见面时,他们回答“没有”,因为对他们来说,“见面”(meet)必须交谈,而且知道对方姓名,至少名字,而不只是介绍而已。但是就问卷上看,他们的“殳有”却会被解释为“不曾见过面”。施测的研究人员非常气馁,在研究过程中,他没有办法加以考虑其他额外所获悉的资料,或将他所获悉的资料用来影响预定的结果(Abbott,1968)。[12]
这种问卷的设计使教育民族志学者不相信问卷。假如事先就认定问题对答题者的意义的话,他们也不相信自问卷衍生出来的量化结果。[12]当然也有许多民族志学者也采用问卷。但是他们的问卷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是经过充分参与和观察之后设计而成的。比如美国人类学学者沃尔科特(Harry F.Wolcott)在1973年出版了《校长办公室里的那个人:一部民族志》(The Man in the Principal’s Office: An Ethnography),是对一位小学校长在履行校长职务过程中的日常行政行为及其角色扮演进行了全面展示及深刻诠释。为微观民族志研究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可以说是一部教育民族志的经典著作。沃尔科特的研究是以民族志方法,在长达两年的研究结束之前,设计了一份长达十页的问卷,请该学校的教职员填写,以收集普查性的资料,包括:每位老师对学校的看法、学校所在社区的看法、所教的班级的看法、对校长一般性的看法、所期望的理想校长的看法等等①。
总之,教育民族志研究者是以“参与者”的角色反复地、深入地参与观察,去发现问卷调查、一次访谈或座谈所没有涵盖的隐性的文化或价值选择。在此之后,教育民族志研究者再进行定向理论的研究,尽管提出理论的时间和周期较其他方法更长,但是,其本身所提出的理论是在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中形成,无论提出的政策建议还是方法指导都更加符合被研究者自身的需求。可以说,以“被研究者”为主体的研究成果与教育实证研究围绕“研究假设”得出的结论之间的差异也就不言自明了。
四、教育民族志的整体性与局限性
(一)教育民族志的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