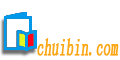浅析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类型
浅析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类型
摘要:张爱玲的人生之路是悲惨而孤寂的,可她的创作之路无疑是成功的,在她的笔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她们或可怜、或可恨,但最终她们都只是屈服于男权的一群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本文粗略的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一个归类。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形象 悲剧形象
张爱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在这个天才女作家的笔下,塑造的最多的便是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例如其中有为了婚姻煞费思量的白流苏;无力反抗却又不甘,最终抑郁而亡的冯碧落;彻底的物质主义者,为了享乐可以牺牲一切的 梁太太……张爱玲曾在《传奇》再版序言中说过“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都是她的家。” [①]张爱玲称这些女性为“蹦蹦戏花旦”那样的女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打定了主意,就会夷然地生存下去。是的,张爱玲的笔下并没有所谓完美的女性,有的只是一群追求各种欲望的女性;只是一群面临封建社会的压迫、残害而努力、小心地让自己夷然活下去的女性。本文粗略的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一个归类。
一、 柔弱的“菟丝花”
柔弱的女子都好似菟丝花,大多是以婚姻为最终目标,依附于家庭这棵大树上。《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说过“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此话虽过分,但是,“对于一种无爱或者一个不以爱为前提的婚姻,对于以结婚为立身之本的‘女结婚员’,他说出了实话,道出了真相。” [②]这些女性可以不要爱情,可是她们需要找能够支撑自己的支柱,因为婚姻是她们唯一的事业,于是她们心甘情愿地成为菟丝花,依附丈夫或物质金钱而生。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这些女性形象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成为了缠绕于寄主身上的藤类,无法追求自由也不想追求。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新式女性”,她敢于面对自己失败的婚姻,毅然地离婚回到娘家。可是她骨子里还是非常传统的女性,她渴望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生活的窘境。因为白公馆不是能让她寄生的地方,那里的一切只会带着人一起沉下去。“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正是这种消磨青春的日子让流苏挣扎与反抗,她唯一的出路,是赶紧找人另嫁,此时,她遇到了浪荡公子范柳源。范柳源是什么人?“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这样一个人,只是想要找个情妇寻欢,而不愿意承担丈夫的责任,来组建一个家庭。范柳源看中的是肉欲的享乐,流苏则看中了他的财富,想要找一张长期饭票。在这场财与色的交易中,范柳源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如果不是那场战争,流苏未必会得到她最终的目标——婚姻。正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说“《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③]可见,这两个人“多多少少都是没有心的人,只会为自己打算的人。”[④]即使有了婚姻,两人的关系仍旧不会有过多的改变,然而这其中却有了让白流苏心安的部分,那就是婚姻及其带来的物质。《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没有流苏出走的勇气,于是她拒绝了与言子夜一同走,虽不愿却主动化身成了菟丝花。“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她抑郁而终,可是她的悲剧并没有因为她的死亡而终结,而是延续到了儿子聂传庆身上,她的丈夫因为她的缘故迁怒于聂传庆身上,于是“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他跟着他父亲二十年,已经给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如此的结局不免让人叹息。如果说前面的例子还有被迫的因素,那么《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却是心甘情愿成为菟丝花,依附着别人提供的金钱和乔琪提供的婚姻。她爱乔琪吗?或许。可这份爱只是她留在香港成为交际花的一个借口。当她初入梁府看见衣柜中各式各样的华丽衣物时,忍不住偷偷地试,虽然意识到“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可终究被诱惑了,“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衣香鬓影无不刺激着葛薇龙的虚荣心,她舍不下富裕享受的生活,可曾经所受的家庭道德教育又束缚着她,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她痛苦,难以抉择,而“爱情”恰恰给了她一个留在香港的理由。她与梁太太最大的不同,也正是她痛苦的根源,就是她的“不彻底”,既不能做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又不能做一个回归传统的女孩子。爱情与婚姻则成为了最终的那块遮羞布。
这一类的女性充斥于张爱玲的笔下,饱含着悲剧意义,只因“她们都明白女人的处境,都善于施用心计而获得她们想获得的男人,在托之终身的同时她们的心身又常常浸在莫名的苍凉与无奈之中。” [⑤]
二、 压抑的变态者
在张爱玲的笔下,还有这样一类女性,她们被物欲和情欲逼成心理变态的一些压抑的变态者。她们无从解脱,只能沉沦于心理变态的怪圈中。《金锁记》中的七巧正是变态者中的典型。
为了姜家的财富七巧嫁给一个残废了的姜二少,姜家又因为她低下的身份而瞧不起她,这种没有温度、没有感情、甚至可能连男欢女爱都没有的生活她一过就是三十年。“她的青春年华,她的无法遏止的欲望,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消耗殆尽,凋萎了,枯竭了。” [⑥]她想爱,她追求季泽,可最终看穿了季泽的真面目;她想恨,她埋怨兄嫂,可那些终究是她的骨肉亲人。爱不能爱,恨无从恨,无法解脱。于是那卖掉她一生换来的几个钱成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当人生所有的欲望都比不上金钱时,七巧就戴上了黄金的枷锁,她的人生也就成了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如果说七巧的前半生还有可怜之处,那么她的后半生则是可恶了。那时的七巧完全是一个疯子,她用变态疯狂的方式来报复,可是举目四望,她又能报复谁呢?只有她那对瘦小单薄的儿女。看看她都对儿女做了什么?因为儿子长白“在外面赌钱,捧女戏子”,“后来渐渐跟着他三叔姜季泽逛起窑子来”,所以七巧不得不替长白娶亲,“娶了一个袁家的小姐,小名芝寿。”可是对这个亲自选定的儿媳,她并不宽厚。成亲之日当众奚落,婚后更是百般羞辱。她让儿子整夜伺候抽烟,打听儿子儿媳的私事,并把这些事宣之于众,最后甚至“变着方儿哄他吃烟”,送丫头给长白做小,这种种的行为无非是为了拢住儿子,因为“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从中可见七巧的心态已然是歇斯底里了,可是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也没能留住儿子,芝寿死后丫头被扶了正,可是也自尽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如果说七巧对长白的种种作为还能说是寡母对独子独占欲的变态心理,那么对长安的精神摧残和践踏则令人匪夷所思。因为长安与表哥的嬉戏,七巧耳提面命“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轮到你们手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上人的当——叫你以后提防着些,你听见了没有?”;为了长安不乱跑,甚至兴起了裹脚的念头,长安的疼痛、外界的笑话,仅仅是七巧的心血来潮,“一时的兴致过去了,又经亲戚们劝着,也就渐渐放松了,然而长安的脚可不能完全恢复原状了。”;为了与大房二房比赛,送长安进学堂;为了女儿“失落了枕套手帕种种零件”,七巧又“闹着说要去找校长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