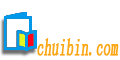苏州博物馆建筑赏析
苏州博物馆建筑赏析
5月27日,从杭州至苏州,入老城,行走观前街一带,未见高大建筑,满眼灰蒙蒙乱糟糟的,想必保护古城风貌是很不容易的。匆匆而行,没有深入,不见憧憬中的水巷乌篷,亦不闻吴侬细语。蓦然,白墙灰框 — 熟识的香山饭店曾经使用过的符号出见了,无须打探,贝聿铭先生的苏州博物馆就在眼前。
第一个令人惊讶的是博物馆的大门。没有想到,享誉世界的贝老先生,他收山之作的大门,竟是如此简单,简单得有如小孩画的简笔画,就是一个墙的豁口,加了一个两面坡的棚架一切文化的、历史的、门第的、或“意味”的装饰通通去掉了,门,只是供人出入的、一个内与外的界限,仅此而已。
进门即是前庭,满目还是一个“简”,粉墙围合出来的一个敞庭,中轴通道铺的是青石板,不走人的地方铺的就是碎石,一棵树、一根草也没有。前庭除了拍照之外,游客显然是无需停留的。
门厅立面稍复杂一些,钢架玻璃,冷冷的,只有门洞才可窥见圆门 — 中国园林的影子(图左)。入门厅,面积不足200㎡,中空,高窗,采光充足,除一个悬吊的钢框吊灯之外,没有任何装饰。北向用玻璃开穿墙面,可见后院景色(图右)。看来门厅的功能定位,只是满足小规模人流的分流和稍事休息。
门厅左、右延伸出通道,天窗,透过格栅撒下敞亮而柔合的阳光(图左),两侧布置展室。通道延至建筑的东、西端点,有对称小中庭,设结构难度很大的悬挑楼梯通达二层展区(图右)。通道由此垂直北折,形成马蹄形主体建筑平面。所有展室都按参观流线布置,路线秩序流畅,极为专业。主体建筑内没有一件多余的细节,也没有任何隐喻“文化”或“历史”的痕迹。
后院以水塘为主,方形硬边,全无遮挡曲折,水面一览无余,架设一座宽宽的石板栈桥,通向一个笨笨的观水亭。俯看,水中只有几片不大的睡莲。紧贴高墙,有叠石,但其形完全不是苏州特产的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倒象老外眼中的中式山水画卷,用几块大小不一的山岩以远近之法布置,“山”水之间,竟无土、无草、无树、无花,而是以洁白的碎石一铺了事。
转了一圈,发现这里所经营的一切都是“极简”的,极至到添加任何东西都是多余的,而减去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的。这令我不敢对这种“极简”轻易评论。
于是,再看一圈,细细体验之后,惟有真心实意向贝老爷子鞠躬的份了。
我把苏州博物馆与我去过的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科隆路德维希现代美术馆并置比较,因为,这三馆都是用于文化展示的现代公共建筑。(而利用皇宫或旧建筑改建的博物馆,在建筑形式上与新建筑不能进行同类比较。)比较的结果,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建筑的内部空间从属或服务于文化展示,建筑本身是不折不扣的功能主义的产物。如果说“蓬皮杜”还有一层形式主义的外壳之外,“路德维希”则是将建筑形式退隐到无需记忆的地步。留连在苏州博物馆里,感受到极简主义在这里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比如院墙、建筑外墙、内墙一统都是粉白、青石勒脚,所有门套一律青石,人行通道还是一水的青石,内外一体,拒绝一切多余的表现。
所有窗、洞、屋架、格栅,都拒绝雕饰;所有的细节并不提供欣赏的形式,而仅仅只是构造必需。
这种“极简”的设计处理,使所有的构造形式都在视觉中后退,退缩到它们纯粹的结构使命中。于是,建筑空间仿佛在退隐,只留下玻璃橱窗中的文物在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这种对文化持有的尊重和谦虚,甚至不惜让自已设计的作品形式退隐,是真正大师者的胸怀。而他们力求隐去的东西,恰恰成为我们回味和研究的对象。
如果将毗邻的拙政园与苏州博物馆作一下比较,就会发现一些令人可以思考的地方。
拙政园当然是苏州园林的精粹之处了。楼榭亭台,曲径折回,间布嘉木奇石,其“山”水之间,意境重重,无一处不是心机智慧所在,荟萃了“邻于自然”的雅致的人文理想。但是,毕竟是摹拟造境,可感的“自然”魅力尚逊于小雅韵致。
而咫尺之遥的苏州博物馆则不然,它拒绝了“小雅”的苏州园林传统,一切小巧的、精致的、玲珑的、符号的东西都被排斥在外,却着意于“空”的营造。前面提到的建筑自身在视觉中的退隐,即是一种“空”的方式;而大“空”的营造,则体现在后院的极简处理方式上。不妨试想一下:当人们行进在室内展区时,由于极简的构造形式使建筑空间在视觉上退隐,这些形式本身不足以成为人们审美欣赏的对象,这种设计上的故意,致使人们的球眼只关注室内空间唯一的主角:陈列的文物。于是,人们只能专注地与文物对话,接受各各不同的、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所传达的相关历史信息。
当人们结束了室内展线的巡游,即顺势由出口被导入室外空间,这就是后院,豁然开敞,院墙将后院从城市空间中分离出来,除了墙头少许的丛绿和兰天白云显示着生动的自然,后院的水、石、小亭、包括地面铺装都简单得难以引起人们的审美情趣,一切人工的痕迹都在压缩、退隐,甚至拒绝草木,这又是一种设计的故意,旨在视觉心理上营造一种“空”,这种“空”,没有“时序”的概念,也没有“历史”的标签,而类似于“禅境”,只不过,不是靠心灵的省悟而达到的那种精神上的澄澈之境,而是用物质的方式营造的素洁的澄澈之境,它不为人们提供任何可以引起审美观赏的细节,只是提供静默观照历史的空间场所。
于是,人们来到这里,由于心无旁鹜,只能做一件事,就是任由那些在室内展馆中获得的种种信息在这里连成历史的块片,从而获得对于历史的体味和认识。这种非“历史”特征的空间营造理念,由于排斥了历史“观”(主观认识)的人文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痕迹(形式“特征”),得以让人们在纯粹的“空”里,客观地、自主地、自在地回味和认识文物所传达的历史。
作为公共文化建筑,贝先生没有忘记挥洒神来的一笔写意,在一个夹院中,巨大的青藤曲卷缠绕,攀着钢架向对角延伸,再舒展地落下,犹如苍劲而又酣畅的水墨大写意。(图12)
博物馆高高的白墙阻隔着今日的苏州城貌,它自成一体空间,尊放着苏州的历史遗存。无论是出自对历史的尊重,还是出自提示一种阅读历史方式的需要,或是出自贝先生的建筑理念,苏州博物馆最终出落得有如象风清月白中的白莲一样,静静地飘落在古城之中,那么安详,那么清素。
作为历史文博的公共建筑,贝先生以“极简”、“退隐”和“空”的营造手法,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我们正处在一个空前的、极度奢侈的建筑时代。是标签文化、伪历史的低能观念和经济的、政绩的需求催生着这种奢侈。这种奢侈的建筑风气,又派生出夸张的、形式过度的建筑垃圾。“存在决定意识”,如果不走出这种风行当代的建筑意识,那么,我们将不可能获得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评价苏州博物馆。
不能进入客观评价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审美经验的惯性。经验是靠敏锐和思考而获得的,保持敏感将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断进入更广、更深的层面,失去了敏锐,只能屈从于经验的惯性。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对“意外”的敏锐远比经验的惯性重要得多。
贝先生的苏州博物馆对于国人(包括建筑家)都是一个“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