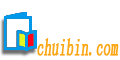儒家对正确处理家庭关系的启示
儒家对正确处理家庭关系的启示
内容提要:儒家学者视正确处理家庭关系为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和起点,并根据每个人面临不同的家庭角色而提出不同的处理家庭关系的办法,但对儒家学者而言,处理家庭关系的不同办法之中,涵盖着一以贯之的道理,即适度的爱。儒家学者从提倡适度的爱出发,提出了种种处理家庭关系的建议主张,这些主张的某些具体内容在现代社会可能有不适应之处,但从其总体精神而言,则颇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本文拟从这一认识出发,对儒家正确处理家庭关系的总体精神进行粗浅探讨,对我们现今如何正确处理家庭关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 爱 忧 乐 适度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人自出生以来,就总是被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在这一切社会关系之中,家庭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处于最原初和最重要的位置:一个人自其出生以来,首先是以子女的身份进入到一定的家庭之中,之后才逐渐与其他社会成员发生联系并成为社会关系的节点之一。儒家由这样的认识出发,将正确处理家庭关系视作正确处理社会关系,乃至维持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无论是“家和万事兴”的儒家式的箴言劝告,亦或者是儒家经典文献《大学》将“齐家”置于“修身”向“治国”和“平天下”的连结点上,都说明在儒家看来,家庭是个人向社会过渡,使得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的关键所在,正确处理家庭关系是通向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和起点。[2]也因此,儒家学者两千多年来一直就如何正确处理家庭关系孜孜以求的进行种种深刻的思考。对他们的思考进行回顾和反思,对我们现今思考如何正确处理家庭关系,是有非常重要的帮助的。
一 爱是正确处理家庭关系的基础
在儒家学者看来,家庭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起点和基础。《易传·序卦》描述社会的形成过程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夫妇。”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儒家学者将所有的社会关系概括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种社会关系并称之为“五伦”[3],而在五伦之中,前面三个涉及到家庭关系,儒家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可见一斑。此外,在儒家学者看来,家庭关系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不仅如《易传·序卦》所展示的那样具有原初性的意义,更具有的是基础性的意义,《颜氏家训》说:“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由此可见,儒家将正确处理家庭关系看作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和根本。
在这种重视下,儒家对如何正确处理家庭关系做出了深入思考,提出了种种具体而微的规定和建议,如在正确处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提出的“父慈子孝”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引下,又提出了种种十分具体细致的主张[4]。但因为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已经不是前儒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所面临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和前儒们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针对当时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的建议和具体内容,例如遵守“三年之丧”的礼制之类,这样的具体措施已不能适用现今时代,因此,在取舍儒家学者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家庭关系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建议上,我们首先有必要剥离前儒提出的具体措施,进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学者留给我们的传统思想遗产之中,有没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以贯之之道,能够为我们所吸收与借鉴呢?
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明确的告诉自己的学生曾参“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个一以贯之的“道”,曾参理解为忠和恕(“忠恕而已”),也可以概括为“仁”的思想。仁是儒家学派的核心观念,也正是仁的提出,讲儒家和传统的周礼提倡者以及其他先秦思想学派区别开来[5]。
当然,对仁是什么,孔子针对不同禀性的学生有不同的回答,但究其根本而言,仁是爱的另一种说法,例如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对此冯友兰先生指出,爱是仁的根本内容,也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准则。[6]
这种爱,根据个人所处的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位置,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父母对子女的爱表现为慈,子女对父母的爱表现为孝;兄长对弟弟的爱表现为友,而弟弟对兄长的爱表现为悌等等,但综括而言,这种爱首先必须体现为一种真实的情感和真的性情。对此孔子说: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上述两例,第一例中,孔子指出,如果没有“仁”,没有真情实感的充实,礼和乐这些东西就会是空洞的。第二个例子中,孔子指出,对父母“能养”,即提供生活上的物质条件并不是孝顺,如果仅仅是“能养”,并不能区孝顺父母和养狗、养马的不同,孝或者对父母的爱,是在能养的基础上,对父母发自内心的尊敬。
在强调爱的真情实感的性质上,孔子特别反感虚伪,他痛斥“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同时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刚毅木讷的人,也就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虽然可能不是仁人,但是真实的人,一个真性情的人,就是与仁接近的人。但巧言令色的人,即那些擅长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人,大多数都是虚伪和虚假的,对与他接触的对象而言,是不可能有真爱的。
对如何理解爱的真情实感,《论语》中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有助我们理解儒家对爱的真实性和切己性的强调。这个例子是孔子和弟子宰我关于仁的一次争论。按照周礼,父母死后应该服丧三年,但宰我怀疑“三年之丧”的必要性,认为服丧三年太久,会对社会生产造成破坏,对此孔子向宰我质疑,如果不服三年之丧,作为子女能否感到心安?宰我回答说能够“安心”,孔子也就只好回答说“你心安就去做吧”(“今女安,则为之!”),但在宰我出去之后,孔子立刻十分严厉的批评宰我“不仁”,其原因在于,孔子认为,子女生下来三年之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子女必须服丧三年,但这并不是对爱进行等价交换式的算账,孔子生气的是宰我对服三年之丧的漫不经心,“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换而言之,在孔子看来,之所以服三年之丧,是因为我们对失去父母之后,对父母的爱的不能释怀,三年之丧的根据不是周礼的强制性规定,而是对父母爱的表达。
二 爱是包含忧乐的情感[7]
仅仅强调爱必须发自内心,既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爱,更不足以让我们处理家庭关系时,将爱的原则正确的予以运用。在现实的家庭关系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种种真爱表象出来的困惑:如因为不能正确处理男女之爱,为情所困或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自杀,或将所爱的人杀死的例子比比皆是;又如父母对子女过于溺爱而所求必应,或者教之过严,事事关心以至于子女产生逆反心理而称之为“父母皆祸害”[8],这些爱毫无疑问都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但真实的爱何以结出的是苦涩的果实呢?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仅仅停留在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而对这种情感何以然并无所知,在这一点上,儒者们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儒者们的答案是,爱是某种包含着忧与乐的连续性的情感。
也因此,儒家在描述爱的情感体验时总是忧与乐并举: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
忧和乐是我们在面对所爱对象时,体会的最直接和最强烈的情感,这毋庸过多说明:例如,每个人面对父母越来越老的时候总是喜和忧参杂着,一方面为父母的还在身边健康活着感到由衷高兴,但高兴的同时,又总会不由自主的为他们或许在某一天突然离开忧心忡忡;同样,在面对子女的时候,我们会快乐他们每一天的健康成长,但又无时不刻担心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意外伤害;或者在男女情爱关系上,我们会发自内心的享受所爱的人陪伴身边的快乐,同时又不可避免的担心他(她)们会不会在某一天爱上别人。
爱的情感体验总是在忧乐之间摇摆不定,这种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痛苦,特别是“忧”的感受,总是让我们的心悬停在半空之中,很多人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使自己的爱走上歧路,但在儒家看来,对忧的这种不确定性感到痛苦,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忧对爱的价值:忧恰好是爱存在最直接的证明,忧是自己对所爱对象的切己的关切,正是对他人的忧,自己和他人的情感联系得以确认。我们对所爱的对象产生担忧,正是基于切己的同情感和命运一体感。不爱,所以不会为之动心,不会为之担心或者欣喜。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遗忘和不在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儒家将忧视作仁,也就是爱的起点,例如孟子认为人心内在的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品德的种子并将之称为“四端”,而“仁”在人心中的道德种子,正是“恻懚之心”,也就是见孺子入井的不忍之心或者说是同情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