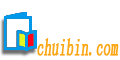从韩国人参丸事件反思我国药物临床试验中的法律问题
从韩国人参丸事件反思我国药物临床试验中的法律问题
【内容提要】从2004年由受试者李秀萍引发的北京地坛医院“胸腺核蛋白试验事件“,到最近媒体报道的海宁市“韩国人参丸事件“,笔者发现目前伴随着跨国药物临床试验项目在国内数量的剧增,引发了出许多与受试者权益保护相关的话题。笔者希望通过本文警醒医务行业关注受试者的权利问题,同时也希望在国内尽早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药物临床试验赔偿机制。本文分析了药物临床试验的法律属性,阐述了受试者与研究者的特别权利义务关系。在此基础上指出,目前我国药物临床试验存在哪隐患,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最后呼吁在国家立法对药物临床试验强制保险基础上,实行无过错归责制度,以确保受试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关键词】药物临床试验 知情 同意 无过错责任原则
在体健普查中,海宁市的沈新连被查出患有腺瘤性大肠息肉(容易导致癌变)。海宁市中医院的医生说服沈新连参加了一个名为“人参预防大肠癌研究项目”的试验性科学研究活动。据医生介绍,人参属保健品,服用后对大肠息肉能够缩小甚至消失。沈新连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在沈新连看来,参加这样免费吃人参的活动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从1998年10月开始,沈新连在当地卫生院医生的监护下,每周免费服用两粒人参丸。沈新连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参加到了韩国一家机构进行的药物试验中。到1999年7月,沈新连已经感到头痛、头晕,检查的结果是高血压。但医生否认了高血压与人参丸的关系,于是她仍旧一次不误地服用人参丸,直到2001年三年试验期满。2002年3月,沈新连已经不能干农活了。据说沈新连吃饭的时候,连手里的碗都会突然掉下来。还经常出鼻血,很多次早上起来,嘴里都是淤积的鼻血。2004年2月23日,沈新连在被病痛折磨了2年多后,肾脏彻底坏死,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离开了人世。最终,沈新连的子女叶沈明将负责药物试验的海宁市中医院告上了法庭。但判决让叶沈明非常失望。法院认为“人参防治大肠癌研究项目”是经过有关部门立项审批的,属于正常的研究活动。沈新连在服参过程中怀疑其高血压与服参有关并向研究所反映时,研究所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尽了自己的义务。而在此后的服参过程中,沈新连也没有向研究所反映有不良的反应。沈新连死亡后,家人也没有向有关部门要求进行尸检。因此法院认为,造成沈新连服参与死亡间的因果关系无法查明,过错在于原告叶沈明一方,判定叶沈明败诉。
1 药物临床试验的法律性质
对医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进行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没有人类不断的试验,就没有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医学史上的任何一项成就,不论通过体外试验的动物实验创立了多少假说,也不管在在动物身上重复了多少次试验,在广泛应用到临床之前,为了确定新药的疗效和安全性,在虚拟人体出现以前,依然必须在人体(患者或健康的志愿者身上)进行新药的系统性研究,以证实新药的药理作用。根据《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指任何在人体(患者或健康志愿者)进行药物的系统性研究,以证实或揭示试验药物的作用、不良反应及/或试验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目的是确定试验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可见,药物临床试验是一种特殊的医疗行为,是一种实验性医疗行为。“韩国人参丸事件”中所涉及的药物临床试验就属于典型的实验性医疗行为。
实验性医疗行为,也称人体试验(Human Experimentation),是指以开发、改善医疗技术及增进医学新知,而对人体进行医疗技术、药品或医疗器材试验研究的行为。其试验的目的在于确保医疗技术、试验用医疗器材、试验用药品对于保健医疗方面有无益处,及是否具有预期的效能。那么,药物临床试验作为特殊医疗行为,究竟特殊在哪里呢?首先,药物临床试验实施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新药对人体的药理作用和不良反应,是新药获得上市销售的前提条件,而对受试者的直接治疗目本文源自六维论文网的居于次要地位;其次,药物临床试验是使用危险与疗效均属未知的新药物或新技术,试验结果无法依靠人类现今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得出必然的结论;第三,在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履行了充分告知、谨慎实施监测义务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发生了药害事件,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会提出其无主观过错的抗辩;第四,即使患者作为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往往患者无法证明服用试验药品与自己目前的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另外,药物临床试验无疑是对人体构成一定风险的医疗行为。回顾人类药物临床试验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过去被用于治疗疾病的有些新药,随着人类相关医学经验及知识的积累,被发现对人类并不都是有利的。有些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被发现,或上市适用一段时间后被发现其药害性质远远超过治疗所能产生的利益。
鉴于药物临床试验的特殊性和高风险性,国家基于公共事务管理之职责自然要对其许可和实施进行严格的行政管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制定了《药物临床试验规范指导原则》。1998年3月我国参照这一原则制定了《药物临床试验管理规范》并于1999年底正式公布,2003年9月1日又重新进行了修订,更名为《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以下简称GCP)。2004年3月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办法(试行)》正式实施。这两部立法成为我国有关药物临床试验行政管理的主要依据。根据GCP的规定,申办者有义务按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临床试验的申请。申办者在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批准并取得伦理委员会批准件后方可按方案组织临床试验。而为确保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的权益,成立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必须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伦理委员会应有从事医药相关专业人员、非医药专业人员、法律专家及来自其他单位的人员,至少五人组成,并有不同性别的委员。从媒体对“韩国人参丸事件”的报道,人参丸药物临床试验并未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也未取得伦理委员会批准就草率组织实施,这显然是违反《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必须对研究者、协调研究者和申办者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药物临床试验中医患的权利与义务
医患的权利与义务是医疗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在众多的医患权利义务中,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一方的每项权利或义务都往往映射着对方的相应义务或权利。例如患者有生命健康不受侵犯的权利,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就有尊重和保护患者生命健康不受侵犯的义务,患者有隐私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就有保密义务;同样,医务人员也有人格权利,患者就有尊重医务人员人格权利的义务,医务人员有诊疗权利,患者就有诊疗协力(配合)义务,等等。笔者认为,在药物临床试验中的权利与义务
要格外注意以下内容:
1 受试者的知情权
知情权源于纽伦堡准则(Nuremberg Cod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医师进行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人体试验。在未经告知的状况下,被俘虏的犹太人成了活生生的、惨无人道的试验对象。德国医师在审判过程中,以其人体试验行为符合当时德国现行法律,并对医学研究、医学进步具有重大贡献为由进行抗辩。但是,在纽伦堡审判(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bunal)中人们一致针对人体试验的适用性,得出了包括“使试验对象完全了解试验内容”、“试验对象必须出于自愿”、“所有处置须符合人道主义”、“不可使试验对象遭受不必要的痛苦”等在内的十项原则,即通称的纽伦堡准则。[3]
在医疗法律关系中,患者有权知晓自己的病情、针对病情可以采取的各种治疗方案以及每一治疗方案对自己健康的利与弊。在药物临床试验中,患者也有全面的知情权。例如在 “韩国人参丸事件”中,受试者沈新连在自主决定参与韩国人参丸试验前,研究者必须使其知道试验的性质和目的、持续时间;进行试验的方法和手段;可能发生的不方便乃至危害;他的参与对他的健康和个人社会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药物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的知情权由两个要素构成:
第一要素是信息的揭示。药物临床试验必须制定具体的施行程序,以使受试者在“事前”了解足够的情况。这些内容必须以受试者可以理解的语言记载于同意书上,包括试验目的以及方法、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及潜在的危险、受试者参与的预期时间以及预期试验效果、研究结果对受试者或其他人之可预期的合理利益、其他对受试者可选择的治疗之方式及说明、受试者同意前有提问题的机会、接受试者得随时退出、受试者资料将受到保密的程度。此外也有的可包括受试者如何挑选、试验主持人等等。
应当注意的是,在部分药物临床试验中,告知受试者同意书中未列的一些内容可能会削减试验的有效性,或本身为试验方式的要求(例如双盲法试验、安慰剂试验)。在此种情况下,只需向受试者指明必须是自愿同意前来参加,至于试验中的其他部分得等到试验结束后才能公开。但所有涉及不完全公开的试验只有在以下条款清楚的情况下才能认为是正当的:(l)不完全公开对于达到试验研究的目标是必须的;(2)对受试者没有潜藏的危险;(3)有一个在适当时候让受试者了解试验性质及结果的合理计划。但绝对不能为了想得到受试者的合作而隐瞒潜在的危险性,对受试者提出的有关试验的问题应如实的回答。公开试验内容在某些情况下会毁坏或使试验失效。有些则会给研究者带来困扰,因此应谨慎区分应公开及不公开的信息。
第二要素是信息的理解。这个要素也是目前药物临床试验做的最不到位的地方。传达信息的方式方法与信息本身同样重要。比如:试验者的说明含糊不清或过于简短、未给相当的思考时间,或者缩减受试者提问机会,都可能影响受试者对试验信息的理解而作出不真实的选择。因为受试者的理解力是智力、合理性、成熟性及语言的组合,应该根据其理解能力的强弱来决定传达信息的方式,或书面或口头说明。总之,研究者应确保受试者理解其所传达的信息。保证所提供的资料或说明,能让受试者对有关潜在的危险性及副作用有充分的理解。危险性增加时,研究者说明解释的责任就随之增加。
应当注意的是,当受试对象的理解力受严重限制时,可能需要制定特殊规定——例如:心智不健全或精神残疾情况。应分别依其情况(比如:婴儿和儿童,精神病患者,临终患者以及昏迷患者)进行考虑。如果研究能在心智正常的人身上得到相同的结果,就不能以心智或行为失常者选为受试者,除非研究需要为这些人提供绝无仅有的治疗,否则不得参与药物临床试验,以保护其免遭伤害。
《南方都市报》报道“韩国人参丸事件”时了解到,在海宁市人民医院住院部另一位“试药人”沈小妹,直到沈新连死了,才意识到自己在被当作试验品。沈小妹也表示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做试验,怎么也不会同意的。沈小妹以为是政府关心农村老人,所以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在整整三年中,沈小妹不知道究竟是哪个机构给她服药,也不知道自己每周吃的到底是什么。在“政府福利”的想象中,她心存感激地服用了三年。显然,研究者的药物临床试验行为是严重地侵害了受试者的知情权。
2 受试者的自主决定权
将信息揭示予受试者的目的,在使之能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自主决定。也只有在患者对所提供的信息有适当的了解后,才能作出决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在与寻求医疗服务的过程中,经过自主思考,就关于自己疾病和健康问题所作出的合乎理性和价值观的判断,并根据判断采取是否参与药物临床试验的行动,可谓自主决定权之行使。笔者认为,自主决定权也是由两个要素构成:
第一要素是自愿的意思表示。自愿的意思表示,包括同意与不同意两种结果。受试者自愿同意,是指受试验者自由意志下的同意,亦即受试验者在作出同意的决定时不受其他人不正当的影响或强迫,如何决定是他的自由选择。威胁是指如果他人不同意某件事,他就有可能在身体、精神或经济方面受到危害。例如暗示患者如不参加药物临床试验,就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不正当的影响是指以利诱等方法诱使一个人作出他本来不会作出的决定。例如暗示患者如果参加人体试验就能得到额外的医疗服务或奖金,对于贫困的患者以免除治疗费用为利诱。不正当的影响是一种隐蔽形式的控制。不正当和强迫及单纯的压力不同。人们常在竞争、需要、家庭利益、道德和法律义务、责任、有说服力的理由等影响和压力下作出决定,但这不是不正当的影响或强迫。美国早期进行人体试验时,曾有以在监狱执行的囚犯为试验对象,而因囚犯处于拘禁中,难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即使同意,也常常是基于提早获得假释或期待得到叫好的处遇所为,不能认为是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不能有任何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行为干预或不正当的影响,否则患者所作出的同意表示也是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主张撤销或变更。
第二要素是同意的能力。同意的能力是知情同意的前提,是自愿采取行动和理解信息的先决条件。判定一个人是否有同意能力,标准为何?通常认为包括理解信息的能力和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进行推理的能力,亦即能够处理一定量的信息、能够选定目的和适合目的的手段的能力。在药物临床试验下,同意能力是指能理解试验的程序,能权衡它的利弊得失,能对面前的选择作出评价,能理解所采取的行动的后果,能根据这种知识和运用这些能力作出决定。笔者认为,药物临床试验的同意能力比诸一般医疗行为为高,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尚不能充分了解药物临床试验的性质,不能成立药物临床试验契约,应由法定代理人代为同意。但因药物临床试验行为常发生不利之风险,因此法定代理人代为同意的场合,应以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治疗性药物临床试验为限。
3 研究者的注意义务
研究者的注意义务,也称善意注意义务或保护义务,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是研究者在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对受试者生命与健康利益的高度责任心,对受试者的人格尊重,对研究工作的敬业、忠诚和研究上的精益求精;其二,是指研究者在具体的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研究者对每一受试者、每一试验环节、阶段的试验行为所具有的危险性加以注意的具体要求。研究者对于受试者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可能发生的药害反应、并发症、试验所引起生命健康上的风险性或危险性,具有预见和防止的义务,此层次的注意义务也称高度危险注意的义务。在我国GCP中就明确规定,研究者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障受试者的安全,并记录在案。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如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研究者应立即对受试者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同时报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申办者和伦理委员会,并在报告上签名及注明日期。
4 研究者的特殊干预义务
由于药物临床试验的启动源于受试者对研究者的授权行为,因此研究者的权利通常常服从于受试者权利。但在由于药物临床试验的特殊性和高度风险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限制受试者的自主权利,以达到履行研究者应对受试者尽到的义务和对受试者根本权益负责的目的,这种权利称为研究者的特殊干涉权。
一些药物临床试验具有较高风险,部分可能发生致死、致残的试验,即使受试者出于某种目的同意,如渴望通过虽有高风险但也可能有很好疗效的试验,使疾病特别是某些缺乏有效方法的疾病得以痊愈;或纯粹出于经济目的(往往药物临床试验是免费的,并有一定经济补偿)等,研究者要积极履行特殊干预义务。当研究者通过检查、分析认为,受试者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的健康状况不适宜进行或不适宜继续进行这些高风险的药物临床试验时,就应当给予适时干预。必要时,必须停止或中断药物临床试验的实施,以保护受试者的切身利益。
3 我国药物临床试验中的现存问题
在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进行的试验中,存在的下述问题应当注意:(1)个别地方仅进行口头的知情同意;(2)知情同意书未经伦理委员会审核,或审核后被研究者随意篡改;(3)没有逐一履行知情同意,参与试验的受试者人数与知情同意书数量不一致;(4)知情同意书中包含受试者放弃合法权利,研究者过失责任免责的约定;(5)语言中包含大量专业术语,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6)告知内容过于笼统,言语模糊,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7)试验的益处表述过多,试验风险强调不够,用过分乐观甚至于不科学或有原则性错误的语言误导受试者(例如“该药的安全性和疗效已经充分的证明”、“该药没有任何副作用”、“该药没有预期的不良反应”);(8)缺乏对受试者权利的描述(例如“受试者随时提出中断或终止试验的权利”);(9)知情同意必须在安静、单独的环境下进行,且给受试者充足的时间阅读、思考和询问;(10)格式不严谨(例如签字不规范,没有签字时间,见证人和研究者是一个人,未一式两份;(11)凡受试者无阅读能力或文化水平偏低(例如小学以下),必须由与研究者无利害关系的人作为见证人共同参与。无行为能力人不等独立参与试验,也不能签署知情同意书。
4 药物临床试验的无过错归责原则与亟待建立的保险机制
4.1 药物临床试验的无过错归责原则
根据传统的侵权法理论,对于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往往存在两种: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的设立目的在于救济受害人的同时,对过错侵权人给予惩戒,以避免类似的侵权行为再次发生。药物临床试验中,如果药品生产企业或研究者存在过错导致了受试者的人身伤害,根据侵权行为法的“过错责任原则”,显然应有有过错方来承担责任,对受试者给予经济赔偿。但是,对于药品生产企业或研究者不存在过错,而又发生了受试者人身伤害,究竟该由谁承担责任呢?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往往因为找不到过错方而使案件陷入僵局。目前国内的多数判例,都是依据《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由当事各方均摊责任。但是,此种“和稀泥”的办法往往不能令当事各方满意,特别是患者更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不幸就得不到经济上的救济呢?
在侵权法理论中的另一种归责原则称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人应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分别规定了产品责任(第122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第123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第124条)、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第125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第127条)等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我们可以发现,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设立目的并非对过错侵权行为进行惩戒,而是在于对无法避免的不幸损害、不幸风险(例如高度危险作业、污染环境、地面施工、饲养动物等)进行合理的社会分配和分担,它是以完善健全的保险制度为基础,并通过保险制度而实现此种损害分配的社会化。
笔者认为,在我国完全有必要建立药物临床试验的无过错归责原则,即凡是受试者在受试后发生了人身伤害,无论药品生产企业或研究者是否有过错,必须对受试者的损害后果给予赔偿。但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律适用必须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或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针对《民法通则》第123条“高度危险作业”做出扩大的立法解释,即将药物临床试验纳入到高度危险作业中。
4.2 药物临床试验的强制保险制度
针对药物临床试验导致的药害事件,如果要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就必须强制从事新药研发的药品生产企业等机构,针对起即将进行药物临床试验的产品购买意外险。如果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发生了药害事件,就可以由保险公司先予赔偿。
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风险分担机制可以效仿发达国家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救济方式。世界各国关于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救济的方式各不相同。日本《药品受害救济、研究开发、产品评审组织法》确立有药品研究开发和药害事件救济基金制度,先向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征收捐款以成立基金会,除可对用药人补偿,也可以减轻生产企业的负担,办理不良反应救济的同时,也推广新产品的研发;美国1986年订立的《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确立了疫苗安全及患者基金补偿形式;瑞典的集团保险制度形式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救济基金补偿形式 都值得借鉴。结合我国国情,可以借鉴日本、台湾地区的做法,强制要求从事新药研发的药品生产企业必须为受试者购买意外险。这一制度既能促进新产品的研发,又能保护消费者权益。
近年,跨国药物临床试验项目在国内剧增。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每年有800多种新药进行人体试验,其中基本是以国外新药为主。目前有60多家跨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着近100个项目的一期临床试验,直接参与人员数万人,如果算上大面积的采样对象,至少在50万人以上。国外的医药企业纷纷瞄准中国作为其新药临床试验的原因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进行新药临床试验风险极高,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发生药害事件赔偿金额也非常高。
药物临床试验必须引起我们关注了。笔者认为,《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一部质量较高的立法,但是在法律责任方面明显偏弱。而受试者对研究者提出民事索赔时,又往往因为归责原则而陷于无助。根据风险经济学的原理,避免因药物临床试验风险的方法是减少行为的数量或转移风险。医疗机构减少药物临床试验风险行为而拒绝药物临床试验有悖于医学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转移风险是避免因药物临床试验风险的唯一合理的方法,我国应尽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设立专项药物临床试验风险补偿基金)或保险制度(如设立药物临床试验意外险种),恐怕这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