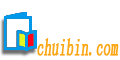汉字六书理论及演变
汉字六书理论及演变
东汉班固、郑众、许慎三家都提到了有关“六书”理论的问题。其中,许慎提出的关于汉字构形的“六书”理论影响最大。此后历代学者对许慎的“六书”理论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索和研究,使“六书”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之后又出现了马叙伦的“六书二系说”,唐兰的“三书说”,陈梦家的“新三书说”,詹鄞鑫的“新六书说”,这些理论对当代“六书”理论的研究及汉字形体学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不同时期“六书”理论的研究展现了各个时期独特的学术风气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指导着中国文字学的发展,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
关键词:六书;六书二系说;三书说;新六书说
引 言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主要有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中国的汉字。然而,目前前两种文字我们只能在文献中看到,只有汉字仍然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交际工具在现实生活中使用。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有自己的特点: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字形和字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透过字形人们可以了解字义。由于汉字的这一特点,于是就出现了有关汉字形体结构的理论。“六书”理论为最早的汉字构形理论,它从确立之日起就成为汉字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核心内容。对不同时期“六书”理论的研究促进了中国文字学特别是汉字构形学的发展。同时也促使汉字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中华民族,甚至是人类文化。
一、“六书”理论的提出及确立
“六书”理论作为中国文字学史上汉字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核心内容,其从提出到确立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
(一)“六书”理论的提出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数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周礼》中记载的“六书”只是作为教国子学习的六艺的一部分内容,并没有阐释“六书”的详细内容。直到东汉时期才相继出现了班固、郑众、许慎等人对“六书”全新的认识。班固承袭西汉末刘歆《七略》而作的《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2]他首次指出“六书”的具体内容,明确地指出“六书”是六种造字方法。郑众注《周礼•地官•保氏》说:“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3]
(二)“六书”理论的确立
东汉许慎确立了“六书”理论。在汉武帝时期,有人在孔子的住宅里发现一大批古文儒家经典。然而,当时所设的博士大都是今文经学派的人,这些古文经一直未受到重视。直到西汉刘歆写了《责让太常博士书》打算立这些古文经为官学,由此拉开了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斗争的序幕。他们把争论的焦点放在经书的内容以及经义的阐释方面,但是由于古文经是用隶变以前的文字写成的经书,而今文经则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的。因此,这场斗争最后集中到了汉字的斗争上。当时的今文经学家并不承认古文字,他们仍然用隶书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及汉字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杜林、班固、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强烈地主张用古文字来研究经书,于是就产生了关于汉字构造的理论。其中许慎的贡献最大。为了客观地、全面地探索经义,使古文经有实际的凭据,他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完成了《说文解字》。该书分析汉字9353个,创立了按照部首编纂字典的方法,为汉字概括出540部。《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字典,也是我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保存了大量的训诂资料、古音资料、古代文化资料等,对文字学的发展及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说文解字》是许慎通过对大量的篆文、籀文、古文等字体的研究所编写的,该书分析了汉字的结构,给出了义例,构建出最早的系统完整的汉字“六书”理论。《说文解字•叙》说:“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4]
总之,班固、许慎、郑众对六书的解说,虽然名称的用字及次序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内容和所反映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把“六书”解释为六种造字方法,在当时影响巨大,因此被后人称为“六书三家说”。后代文字学著作一般采用许慎的“六书”名称,班固的“六书”顺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二、“六书”理论在古代的发展演变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书”理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六书”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消沉期,这一时期的“六书”理论并没有重大的突破。此时大多数学者从事于《说文解字》的研究,出现了大量的字书。“根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记录,这个时期的字书共有123部。”[5]这些字书主要以晋朝吕忱《字林》、南朝顾野王《玉篇》和北朝阳承庆《字统》为代表。《字林》模仿《说文解字》而作,对《说文解字》有所补充。南北朝时期《字林》受到人们的重视,北齐的颜之推把《字林》和《说文解字》并称。《玉篇》是南朝字书的典范,《字统》则是北朝字书的代表。这两部字书从当时的用字实际出发,改用楷书字体,大大增强了字书的实用性。
(二)唐宋时期的“六书”理论
唐代“六书”理论的发展仍然没有重大的突破。虽然这一时期李冰阳对《说文解字》进行了研究整理。但是从实际上看,他对《说文解字》的研究其实是对《说文解字》的篡改,这就阻碍了“六书”理论的发展。李冰阳之后“于文字学有继绝举废之功,当推徐铉徐锴兄弟”。[6]
徐锴、徐铉有“大小徐”之称,其中尤推小徐的成就最高。他提出了“六书三耦说”。他把六书分为三类,指出:大凡六书之中,象形指事相类,象形实而指事虚;形声会意相类,形声实而会意虚;转注则形声之别,然立字之始类于形声,而训释之义与假借为对。《说文解字系传》中写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谓老之别名,有耆,有耋,有耄,子养老,是也。一首者,谓此孝等诸字皆取类于老,则皆从老。若松柏等皆木之别名,皆同受意于木,故皆从木。”[7]徐铉的这些分析涉及到了“六书”中转注的问题。
北宋王安石在《字说》中以会意研究汉字,虽然受到了批评,但是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这对“六书”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北宋王圣美提出了“右文说”。“右文”是相对于“左文”而言的。“左文”和“右文”就是汉字的形符与声符,形符常居左,故称“左文”;声符常居右,故称“右文”。之后王观国在《学林》中提出了与“右文说”类似的“字母”。“卢者,字母也。加金则为鑪,加火则为炉,加瓦则为甗,加目则为矑,加黑则为黸。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则众议该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田。或用省文,惟以田字该文,他皆类比。”[8]张世南在《游官纪文》中也谈到了有关“右文”的问题。“自《说文》以画字左旁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右旁亦多以类相从。如‘戋’有浅小之义,故水之可涉者皆为‘浅’,疾而有所不足者为‘残’,货而不足贵重者为‘贱’,木而轻薄者为‘栈’。‘青’字有精明之义,故曰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溷浊者为‘清’,目之能明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凡此皆可类求。聊述两端,以见其凡。”[9] “右文说”涉及到了“六书”中形声的问题。
北宋张有对指事提出了全新的解说。他根据《说文解字》撰写了《复古篇》,该书辨俗体之伪,以四书分隶诸字,正体用篆书,而别体俗体则附载注中。张有根据许慎所举的例字,针对许慎定义的含混不清,明确地指出:所谓指事,“事犹物也,指事者,加物于象形之文,直著其事,指而可识者也。如本、末、叉之类。”[6]他对指事的全新解说与现代学者们对指事的见解基本相同。可见,张有对指事的解说是相当的精辟的。
南宋郑樵首次摆脱了《说文解字》的束缚,主张“凡许慎是者从之,非者违之”,他以六书为纲统编全部汉字,并对六书本身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开启了六书研究的新风尚。在《通志•••••六书略》中,郑樵批评许慎“惟得象形、谐声二书以成书,牵于会意,复为假借所扰,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学者之患在于识有义之义,而不识无义之义。假借者,无义之义也。假借者,本非己有。因他所授,故于己为无义。”[9]许慎说:“‘能,熊属。’‘能兽坚中,故称贤能’”把“贤能”的“能”与“能兽”的“能”混为一谈。郑樵批评许慎分析的假借与象形的界限不明确。他把文字作为符号来研究,提出了“子母相生”理论。他的“子母相生”理论成为郑樵汉字生成理论的首要理论,也是他的汉字生成理论中极具特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郑樵通过对汉字的分析把六书分为三类:一类是文,“象形、指事文也”。二类是字,即会意、谐声、转注。“会意者,二体俱主义,合而成字也”进一步申发了许慎“比类合谊,以见指挥”的会意字形体结构部件组合成另一个新字的造字方法。“谐声,文合而成字,文有子母,母主义,子主声,一子一母为谐声,谐声者,一体主义,一体主声”。对形声字的研究,他采用读音相同的字作为声符完成了对汉字形体的改造,继承了许慎“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的定义。对转注的研究,郑樵将转注分为建类主义、建类主声、互体别声、互体别义四类,这些分类其实是对汉字的归类。“建类主义”为汉字确立了相同的意义范畴;“建类主声”确立了声音类;“互体别声”是指部件相同,读音不同的汉字,确立了相同的部件范畴;“互体别义”指部件相同,意义不同的类。三类是文和字,即假借。郑樵对“六书”理论提出新的看法,开创了“六书”之学,对后世“六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元代的“六书”理论
戴侗主要从事于对“六书”中假借的研究。他批评了许慎假借的例字。“令,本为号令,命令之令(去声),令之则令(平声)。长之本义虽未可晓。本为长短之长(平声),自稚而浸高则为长(上声),有长有短,弟之则长者为长(上声)。长者,有余也,则又谓其余为长(去声)。二者皆由本义而生,所谓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非假也。所谓假借者,义无所因,特借其声,然后谓之假借”。[9]从“六书”理论确立直到戴侗,关于假借才完全清楚地弄明白。《六书故》中首次提出“因声求义”:“至于假借则不可以形求,不可以事指,不可以意会,不可以类传,直借彼之声以为此之声而已耳。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不可不知也。书学既废,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义矣,未知因文以求义也;训诂之士知因文以求义矣,未知因声以求义也。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8]他阐释了有关词义引申的理论,指出了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之间的联系,对词义系统的研究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为词典编纂,甚至是中国语言学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杨恒对“六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六书”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他继承戴侗的《六书故》作《六书统》,“以凡文字之有统而为六书也,因名之曰《六书统》”[10]。该书收集了大量的金文和籀文,将象形分为十类,指事九类,会意分为十六类,形声十八类,转注十八类,假借十四类。然而由于该书收集的文字形体不可靠,就必然导致了对汉字结构分析和“六书”分类的不准确。
周伯琦认为转注、假借都是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演变出来的。他在《说文字原叙》中说:“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者,字也,转注、假借者,文字之变也。”他把象形、指事归为一类,会意、谐声归为一类,转注、假借归为一类。实际上,他对汉字结构的分析用的并不是许慎的“六书”,而是“四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四)明代的“六书”理论
赵撝谦已经开始认识到“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与“转注、假借”性质的不同。他在《六书本义纲领•六书总论》中说:“六书初一曰象形,文字之本也;次二曰指事,加于象形者也;次三曰会意;次四曰谐声,合夫象形指事者;次五曰假借;次六曰转注,侘夫四者之中也,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象形、指事文也。象形文之纯,指事文之加也。会意谐声,字也。谐声,字之纯,会意,字之变也。假借、转注,则文字之俱也。肇于象形,滋于指事,广于会意,备于谐声,至于声则无不协矣。四书不足,然后假借以通其声,声有未合,而又转注以演其声。”赵撝谦对“六书”的研究启发了后来杨慎对“六书”理论的研究。
杨慎提出了“经纬说”,即“四经二纬说”。他将“六书”划分为经纬两类。他在《六书索引》中对“六书进行了分类:“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假借者,借此四名也;转注者,注此四者也。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6]杨慎对“六书”所作的分类,直接点明了假借、转注不是造字方法,而是对“四象”所造之字的借用、转用。四象为经,假借、转注为纬,经纬交织,便形成了整个汉字体系。他还认识到造字是有限的,但是用字却是无穷的这一客观的矛盾,同时指出假借、转注正是解决这一客观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法。杨慎的“四经二纬说”批判地吸收了传统的“六书”理论,是从自己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思想出发而形成的新的“六书”理论。这一观点使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与“假借、转注”的性质差异更加地明显。他把学者们从以“六书”为“造字之本”的传统轨道上拉开,为后人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明代的吴元满撰《六书正义》、王应电撰《同文备考》、魏校撰《六书精蕴》、赵宦光撰《六书长笺》等都对“六书”理论进行了论述,对汉字“六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清代的“六书”理论
戴震是清代“六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六书”进行了“体”“用”的分类,首次提出了“四体二用说”。[11]《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说:“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冯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形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字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初、哉、首、基皆为始,卬、吾、台、予皆为我,其义轻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12]他认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而转注、假借则是用字之法。戴震的“四体二用说”明确了“六书”的性质。由此,转注、假借与前四种造字之法彻底区分开来成为用字之法。这一重大突破对清代《说文解字》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有“说文四大家”之称的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都采用戴震的“四体二用说”,从形、音、义不同角度研究《说文解字》,分别撰写了《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义证》、《说文解字通训定声》、《说文解字释例》、《说文解字句读》等。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假借、转注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13]
三、“六书”理论在近代以来的发展演变
封建社会的灭亡预示着“六书”理论古代研究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六书”理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开始,也就是近代以来的“六书”理论研究。
(一)六书二系说
马叙伦在“六书”理论发展的历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中提出了“六书二系说”。他说:“指事、象形、会意三书,实皆属于形系;形声、转注、假借三书实皆属于声系。形系者,即此所谓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声系者,即此所谓形声相宜之字。然此明言仓颉造文,其后造字,则非一时可知。度之文化进展之程序,故亦宜然也。……因袭形系之文,而创为声系之字,则形声之书兴焉,其法以形为主义者,则以彼形为声,复可以此形声之字为声,然后相生而无穷矣,故谓之字。”[14]马叙伦先生从许慎所说的“依类象形”和“形声相益”入手,根据形声义三者结合的不同特点和彼此之间关系,将作为造字方法的“六书”分为形系和声系。形系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声系包括形声、转注、假借。
马叙伦的“六书二系说”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他强调“六书” 中的每一书都要具备形音义三个条件。这是对清代学者研究“六书”理论的继承。他们认为汉字就是形音义彼此交错的关系。王筠曾以“字之有形音义” 比喻“人之有形影神”,这个比喻就表达了“六书”理论用于汉字分析所要依据的重要原则;其次,他不仅把“假借”放到了象形、指事、会意之后,形声之前,而且把“假借”看作“声系之首列”。他认为六书的次序是表示文字进展的过程的,而假借是由形符文字过渡到声符文字的第一个阶段,所以“假借”应该摆在第四位。
形系所属汉字的意义一般可以通过汉字形体结构展现出来,而声系所属的汉字则重在对音得关注,以形系汉字为基础,通过语音关系来造字。所以,形声二系之分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二)三书说
20世纪三十年代,唐兰先生首先提出了“三书说”。他在1935年写的《古文字学导论》和《中国文字学》里都提到了“三书说”。此三书即:“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他认为象形文字就是画一个物体或者画一些记号,使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他还认为只要是象形文字,一定是独体的,一定是名字,一定是除了本名以外,不具有其它的意义。象意文字是图画文字的主要组成部分,象意文字有时是单体的,有时是复体的。象形文字和象意文字都是上古时期的图画文字,不同的是象意文字不能一看就使人明白,而是需要人去仔细分析。形声字是由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字,所以形声字比较容易识别。如:“停”从“人”“亭”声。他认为“象形、象意、形声足可以核定中国一切文字”。[2]很显然这个观点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有些字并不能纳入此三书中。如记号字:五、六、七等。
虽然,唐兰的“三书说”存在许多不足,不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但是,他是第一个系统全面地对传统“六书”理论进行大胆改造的人,他的敢于大胆创新的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同时,他提出的“三书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革新,冲击了传统的”六书”理论,开启了当代“六书”研究的新风气。
(三)新三书说
1956年陈梦家提出了“新三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评述了唐兰的“三书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假借字是汉字的基本类型之一,并把象形与象意合并在一起称为“象形”;其次,他认为形声字中形符和声符居于同等的地位,所以形声字不能称为声符文字;最后,他不同意唐兰所定的关于象形字的三个标准。1、他认为象形字分为独体复体是人工的分析,如“有”字从又从肉,然而它依然像手持肉之形;2、象形字不仅是名字(词),而且可以是动字(词),如“不雨”的“雨”是动字,“大雨”的“雨”是名字;3、一切象形字可以有形的分合,义的引申,声的假借”。[15]陈梦家补充了唐兰的“三书说”,对汉字构形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继陈梦家之后,对“三书说”影响较大的是裘锡圭,他的《文字学概要》在批评吸收唐兰、陈梦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陈梦家的“新三书说”大体上是合理的,只是他把陈梦家“新三书说”中的“象形”改为“表意”。因此,裘锡圭的“新三书说”的三书包括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由于汉字是由符号构成的,因此,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声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他又将三书的每一书下分出若干小类:1、表意字分为:抽象字,如一、二、三、五等;象物字,如:火、水、山,相当于六书中的象形字;指事字:如:朱、未、本等;象物式的象事字:从外形看像象物字,实际代表的是事的名称,如:“又”字是指方位的左、右的本字,分别以像左手和右手的形符表示左方和右方的意思;会意字,这类字是指会合两个以上形符来表示跟这些形符本身的意义都不相同的意义的字,大致就是传统“六书”中的会意字。2、形声字分为:①一形一声字,如:何、狮、蛇等;②多声和多形;③省声和省形,如:亭:从商省,丁声。3、假借字分为:①无本字的假借,沙发、巧克力、可口可乐、肯德基、布尔什维克等外来词;②本字后造的假借,师―狮;③有本字的假借,艸―草。裘锡圭对“象形、假借、形声”的分类,使其条理清晰,合乎逻辑,这比传统的“六书”理论的分类更好。
(四)新六书说
詹鄞鑫在《汉字说略》中提出“新六书说”。他不同意裘锡圭有关假借的观点,他认为假借字不属于汉字的基本类型之一。同时,他还认为分析汉字结构就是分析孤立的静态的汉字的造字结构,并不需要针对汉字在文献中或者动态的语用中的不同用法而作不同的处理。詹鄞鑫在对前人研究的批评继承的基础之上,他将汉字结构类型分为六类: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即:“新六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