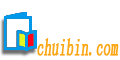
上述这样的句段,这样的陈述仿佛是一些真正的废话,在下一段的语义前寂寞消失。它等待的是读者在文章整体框架内的识读与理解,多少增添了语义的不确定性及迷乱的成分,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障碍,但正是这种“恍惚美学”构成了他在先锋浪尖上的特殊景观,冷漠、孤独、颤栗与滚动的语言氛围。
在经历了这一阶段的“危险”探索后,长篇小说《施洗的河》迎来了北村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北村与第一时期的语言范式决绝了。这一时期,北村从技术迷津中冲出来,坚持用心灵的质量敲击世界,作品致力于精神向度的重建。北村在余华的绝望主题之后,重新在悲凉中抚摸了心灵的热度,继而将这一主题生发开去,构成了先锋小说的一个新的高度与起点。这时我们再也找不到北村过去的那种指向的过于明确和恍惚迷离间的矛盾,其精神指向有了明确的对象,与其他先锋作家分道扬镳。接着,在这一阶段的小说《玛卓的爱情》、《周渔的火车》、《强暴》等反映爱情、生活的主题时,表现了对失爱主题的阐释,直指上个世纪民众的精神危机,在出示了一个个痛楚的人生经历、恋爱过程后,北村告诉我们“爱情的不可能”,这不亚于人类精神命运的刀割与剖白。在这一阶段我们看到了北村的冷酷,使每一个看过他作品的人都被其中阴郁的气氛“吓”得“毛骨悚然”,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北村出示的生存和精神窘境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便是北村的高超吧。在爱情生活上,我们“经历”了背叛(如《周渔的喊叫》),爱情本身的脆弱与生活实际的矛盾(如《强暴》),爱情的乌托邦与生活的无法沟通(如《玛卓的爱情》)……我们被一个个残忍的生活碎片击倒,但又在击倒在地的时刻反思我们的精神境遇。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写作风格上,擅长怪异的比喻,脱离了第一时期恍惚的语言模式,用琐碎的短句结构文章,在快意残忍的语词驱谴下,嗜好悲剧,并且永远弥漫着不祥的气息,死亡充塞于每个角落。他笔下的人物是坚决不可能投入到尘世的怀抱,从而避免精神的拷问,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结尾处义无返顾地奔向了肉体的毁灭,精神重获的“葬场”!如在《玛卓的爱情》中的描述:
我想象我和他一起生活,在很远的地方,那地方连汽车都没有,也没有马车,只有木屋与黄花菜地,他种田我织布,太阳出来时,我坐在轮椅上。
我们不会生活,你看生活被我们弄成这个样子,一定有一个安慰者,来安慰我们,他要来教我们生活,陪我们生活。
----《玛卓的爱情》
《愤怒》是标志北村的写作进入第三阶段的作品。作品不再把目光拘泥于人物缠绵纠葛的爱情生活,而把指针指向了更为现实,更为广阔的境遇,关注于弱势群体——民工的生活,以极大的人性关怀投入到了写作中。正如之前朱大可所预言的那样:“北村已经走向他自己的末日,这是不容质疑的。沉浸在黑暗的结局里,说出对世界和自我的厌倦,仿佛一种极度的杀气,在聒噪的舌上一闪,去擦击出信念的火焰。在北村的尸骸上,北村正在复活。这说出了两个事实:‘新潮’小说的死亡和一种更接近灵魂的有力话语的诞生。”②
完全如此,北村正在自己的灰烬中复活。《愤怒》为我们见证了这一点,这一力作的成功突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作品中溶入的新鲜血液。“积跬步,致千里”,北村突围了:
第一, 题材的转变。
在跳出了迷津生活、爱情生活的包围后,北村将这次“探索”的矛头指向了社会的底层人民——民工。这是当下人最为关注的人群之一,而我们仰视的目光往往忽视了他们的存在,现实中的人们感情没有了出口,有的只是经济时代的忙碌与无奈,甚而渐渐地见怪不怪了,是北村的《愤怒》让人们的目光下移了,心灵再一次地陡然跳动,深深切切地看到了底层人民的悲惨境遇,这较之之前的题材便有了更为深沉的力量,北村可谓应时重生。北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一直在挣脱现代主义的东西。当我要写一个人外在的、精神的和心灵的处境时,我必须摆脱原来的那种冷漠的语言,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有神圣感情的人,我对笔下的人物有一个新的态度。在《愤怒》之前的一些作品当中(包括《周渔的火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样的问题,而《愤怒》则是完全明确地摆脱了现代主义的东西。可能有人会问,这么简单的语言有表现力吗?那么我就会告诉他,你不要注视我的语言,而要看我的语言有没有表达重要的信息,即人物的精神层面的感受。这个信息是内部写作达成的,不是外部写作所能完成。内部有一条河流,人性的困难或者心灵的巨大矛盾和希望都在这里。”③从中,我们看到了北村自信的重塑,和他在多年前的写作彷徨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他说:“我立刻获得了一个孤儿的地位,感到茫然无措,道德水准在这个时候开始崩溃……”④因而文章中所表达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即是由爱获得的救赎和走向死亡的明暗对比,让我们更多的接受了爱的普照。
北村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基督教徒,1992年信仰的确立让他的作品中多了信仰的力量和爱的感悟。不由得,这便是他写作风格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诚如他的观点,关注时代的症结正是有良心的作家应该具备的水准,这也让他的写作选材有了更合理的一面。
第二, 母题的变奏。
支配北村小说的母题是简单而单纯的,“逃亡——迷失——死亡”三位一体的序列,从这个结构派生出了北村全部的“者说”系列和之后的“爱情”系列。逃亡是故事的开端,迷失是他们的发展,而死亡则支配了最后的结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各个母题在叙述中的固定位置,母题间的恒常关系,意味着一个基始结构的存在。逃亡是一个杀机四伏的故事的戏剧性开端,迷失是两者之间的重要环节,主人公及每个细小的人物均陷入了庞大的迷失状态中,最后以死亡收场。肉体上的死亡仅是外在形式的身体悲剧,心灵的死亡才是肉体死亡的真正隐语。比如,《玛卓的爱情》中玛卓的死亡;《孙权的故事》中孙权在面临肉身之死时,发现比肉身监狱更可怕的是灵魂的监狱……
然而,这次在《愤怒》中北村却用了“爱”作为了“死亡”的消解,这是心灵上的消解,主人公李百义没有在受到审判的那一刻死去,而是在审判中获得了重生。阴郁恐怖的地狱大门合上了“大嘴”,迎来的是爱的圣洁的阳光。这无疑是一次触目惊心的变奏,看到了“罪”的行径终于可以获得“爱”的救赎。正如《愤怒》文末所描写的那样,李百义接受了法庭的审判,他入狱了,即便当时他是用“自己的罪”洗涮“别人的罪”,用罪行严惩别人的恶,但在最后一刻他接受对自己的罪行的宣判,因为这毕竟带来了对别人的伤害,即便逃脱法律的宣判,但心永远是被捆绑着的,他自认为结局是公平的、合理的。当他在囚车上前进时,街边的标语写着:“凶手脱罪,民愤难平!”时,李百义说:“我下去再鞠个躬吧。”⑤当他在车下遭到鸡蛋、石头甚至大便的袭击时,他忘记了浑身上下滴着的粪水,已闻不到它的气味。当车驶达钱家明墓地的时候,与先前的“愤怒”截然相反,他闻到的不是腥臭的泥土,而是泥土的芳香,这便是超越了“愤怒”的坦然! “……监狱的围墙已隐约可见,朝阳照临它,镀上一层金色光芒。好像天国的景象。”⑥所以,最后一章用“天堂”为题,似乎让每个人看到了爱的惠临,生活充满了希望。
母题在最后一个环节的变奏,变成了“逃亡——迷失——救赎”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