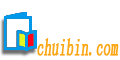
区域位置的比较:我们是偏远的吗?
在前人对贵州的认识和贵州省情的书写历史中,我们可看到不少这样的描述:
贵州建省前,“夜郎自大”之类的典故以及“瘴疠蛮荒”、“蛮夷之地”等形容词,虽不等于对贵州省情的认识,但却影响着后人对贵州的印象。
明代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的王守仁,人黔后写下了“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的诗句;
五四运动前,创办的<少年贵州日报>在<发刊词>中对贵州作了如下概括:“黔居边远,国之奥区。攘攘熙熙,犹有羲轩之乐;迭迭重重,障碍舟车之路。交通不便,进化较迟,唯其然也。故忠厚笃实,犹少时髦浇风,然闭塞晦盲,又成夜郎自大。造车闭户,浑忘辙轨,须造蠡测管窥,恍嫌天地犹窄。抱残守缺,故步自封”。
抗日战争时期,从地理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角度,概括省情,称贵州为“抗战后方”,“陪都屏障”,言简意赅。
在这些历史的描述与书写中,贵州给人留下了“偏僻”、“落后”、“蛮荒之地”的刻板印象。以至今日更有“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的“三不主义”论调,并以此作为贵州省的经济落后的挡箭牌。在全国的大棋盘中,贵州可以说是最没有区位优势的省份,这“三不”确实是对贵州区位劣势的最好注解。
然而,事实上,贵州还有这样的优势:贵州是大西南南下出海的重要通道和陆路交通枢纽。既是四川、重庆南下出海的必经之地,也是华中、华南联结西南的重要通道。境内有川黔、湘黔、贵昆、黔桂和南昆五条铁路干线运营,已建成通车的渝怀铁路也穿越贵州,贵阳是西南地区的铁路枢纽;上海至瑞丽、重庆至湛江两条公路国道主干线穿越全境并形成枢纽。
贵州是大西南最重要的战略腹地。最初贵州之所以建省,并非是出于经济而是出于战略的考虑。自明代,中央王朝引宋时南诏独据一方及元时蒙兵由滇抄宋的史实为鉴,以防滇患为主,从川、滇、及湖广的属地中,各划一块,组成贵州,自此开创了黔作为新兴省份在中国格局中的历史命运。
也就是说,以历史的过程和战略的位置来看,贵州虽非经济上的开发省,但却是西南的几何中心、交通枢纽和重要的战略中心。在中国的大区域经济合作中,贵州对西南市场有着很强的幅射作用。时下,正紧密锣鼓进行的厦蓉高速公路和贵广快速铁路正是基于对此战略构架的实施。而贵州的战略地位,无论是汉武帝修夜郎小道,制服南越,还是朱元璋屯军、屯田,建立贵州行省,以稳定西南政局巩固全国统一;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西南“三线建设”战略,还是80年代至今的西部开发战略,无不证明了贵州的重要的战略地位。
因此,贵州由于地理上的“三不沿”(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造成地理偏僻,区位优势差,导致在全国的发展格局中落后的理由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在贵州新近的“两欠”省情定位中,将贵州定位于是两江屏障;是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是大西南交通要道;贵州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腹地。这一定位,是贵州在走生态文明之路,实现跨越式发展背景下,对省情认识的一种视角,着意凸现的只是省情中与之相关某些特点与要素。
发展理念的思考: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吗?
何为发展?“发展”已成为报纸、电视、广播和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最常见的词。
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术语,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最简单的是:发展是指改善人们的生活。在当下的语境里,人们认可的发展观,是以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为核心,把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作为一个衡量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它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通常以“年”为单位)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为保障人民的生存需要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一定量的GDP就是空谈。
然而,随着全球现代化的浪潮越演越烈,人们逐渐意识到把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的量上的增长,等同于GDP的提高,却是有失偏颇的,其缺陷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地球资源的捉襟见肘以及生态灾难的频繁发生逐渐暴露了出来,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一些欠发达地区在发展的操作层面上,出现了“发展的悖论(paradox of development)”: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展固然会使当地人不满,但发展同样会使他们不安。发展就会有外地来的投资和流动人口。外来投资者总会占用农地、草场、矿山、林木和淡水资源,多半还会污染环境。发展还会大量建立经济开发区和自然保护区,要求移民搬迁,限制当地人对原有生活资源的使用和控制能力。发展还会提高物价,使当地人感觉相对贫困。发展还会造成劳动的文化分工,即因民族不同而产生的工作岗位、就业和收入水平甚至居住区环境上的差别,亦即城乡差别与民族差别重合。发展通常还会带来毒品、性病、艾滋病等公共卫生问题,使当地人感到自己被动受害。最重要的是:发展会使少数民族的语言、宗教和传统文化习俗在自己的家乡也被边缘化,使他们不仅在全国和全社会,而且在本民族聚居区和自治地方也变成文化弱势群体。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援助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建设项目就过多地打上了援助地方的文化烙印而没有顾及自身文化的整体景观。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一些工业企业却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污染。又比如,西部一些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迅猛,结果却使人们感到在当地就业更难。由此可见,失去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目标的发展本身也会从解决问题的杠杆变成引发问题的根源。
“发展的悖论”并不否认:发展本身也是人们的内在需求,并且是国家和地区繁荣富强的前提。例如,没有近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今日中国就没有讨论和谐社会的空间和条件。没有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但发展的悖论毕竟警示我们:在试图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特别是文化认同与价值诉求的同时,我们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综合平衡的理念,必须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来保证人民群众以主体身份来参与发展并分享成果。果能如此,这样的发展不再是发展的障碍或负担,而且会是政治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总之,对贵州省情的认识,就是在多重比较中的认识,其关系到从经济到文化的全方位分析,关系到从现实到历史的深度评估,并且还关系到在世界宏观背景中对不同区域类型和发展模式的相互比较。只有这样,才可能全面理解“贵州现象”;而只有全面理解了“贵州现象”,才可能更为深刻的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且,这既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又是一个价值论问题,更是一个有待操作的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