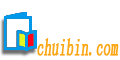
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调查研究报告
托老带少,披星戴月,她们的艰难和辛酸有谁知?
独守空房,担惊受怕,她们的苦涩和孤独对谁言?
忍辱负重,流言蜚语,她们的权益和安全谁保障?
天各一方,后顾有忧 她们何日才能夫妻团聚?家庭团圆?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农村留守儿童;又因为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而开始关注留守老人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一直忽视着一个更为关键的群体?那就是留守妇女!这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既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忍受两地分居的煎熬,还有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她们的生存状况如何?她们在她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的地位如何?她们最想说的是什么?她们最想做的又是什么?带着这些沉重的疑问,笔者走近了她们。
1 劳动强度大,一个顶俩,长年累月的体力透支和生活磨难在她们的脸上刻上了深深的印痕,她们默默承担着,毫无怨言,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伴随着大量男性强壮劳动力背井离乡,妇女逐渐取代男人成为农村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她们一边要赡养老人,照顾孩子,一边要肩挑起全家农活的重担(原本由两个劳动力共同完成的强度)。甚至还要帮扶个别劳动力短缺的邻居和亲戚,农村留守妇女的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她们的辛苦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强壮男性劳动力。
张燕就是这样的一个留守妇女,第一次见到张燕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居然只有35岁,长年累月的操劳在她的脸上过早地刻上了过多的皱纹、暗斑、甚至连皮肤都变成暗黑色的了,背有点佝偻,看上去就象一个50多岁的老人。她告诉我她家共有6口人,两个老人都有快60岁了,还有一个老人生着病,是结核,两个孩子,一个12岁,读七年级,一个10岁,读三年级,因为穷,男人10年前就开始在外面打工,一年差不多就回来一次(来回一次要花费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在上海那边,最多的一年也就回来过两次,那是父亲结核病发作,后来在乡里的卫生院里住了半个多月,好点就出来了,家里有10多亩山坡地,全家人包括牲畜的吃就全在上面了,她一边捋着包谷,一边和笔者聊着"只怪我命不好,但命是天定的,谁能改变呢,他外出打工还是我催他出去的,那时家里紧,揭不开锅,就是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因为不符合生育政策,交了200多元的罚款(社会抚养费),父亲又急又气,就发病了,这都是没法子的事,于是我就催他去打工,当时自己也犯愁,又要照顾老人,又要抚养孩子,还要管五张口的粮,咋整?可不出去不行啊,父亲治病要钱,孩子读书要钱,修房子要钱,于是我一咬牙还是坚持下来了,结果一坚持就是头10年!"看着她的脸,又看看她刚刚翻修好的新房子,我问她:"现在条件要好点了,你还准备让你丈夫在外面继续做下去吗?"她思考了一个,眼神里显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刚毅,然后用肯定而坚强的声音说:"继续吧!我们还有两个孩子,我们得准备好孩子将来读大学的钱,当然如果孩子读书完了,我就要孩他爸歇息着,和我一起慢慢来做这些活路,那会轻松得多了,我还想到他打工的地方去玩玩,他说过孩子大了后要带我去的"那语气分明透露出一丝俏皮和无限的期盼。
2白天辛苦忙农活,夜晚与孤独寂寞相伴,听虫蛙鸟鸣解闷。把思念埋藏心底,忍受着两地分居的情感折磨,一面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多挣点钱贴补家用,一面又害怕自己被抛弃,当无望时,寄希望于迷信或者成为留守的情感牺牲者。
当我走进赵艳芬的家里时,赵艳芬正在和村里的三个女人摆龙门阵(闲聊)。因为正值年关,她们难得都有空闲时间,所以就聚一起了,正织着毛衣的赵小英说"我们平时忙得脚不歇地的,平时没机会聊,晚上又不敢出门,年关也没什么活路了,就聚一起摆摆"于是我问她们:"如果有时间,你们最想做什么,你们最害怕的又是什么?"年纪比较大的赵幺妹说"我如果有时间,我就想美美地睡一觉。"赵春兰和赵艳芬,赵小英都是结婚在五优年之间的,都异口同声的而又各有羞涩地说想给自己的男人打个电话,说说话,赵小英是刚嫁入还不到三年,读过初中,性格活泼大胆,她说"如果我真有那时间,我最想飞到他身边,可是孩子才不到一岁,如果孩子有三岁了,我就让他爷爷奶奶带着,我也和他一起去打工,我才不愿这样守活寡般地活一辈子!"一句话,把我吓得惊了一大跳,但回头仔细一想,这不正道出了留守妇女的一个心声吗?这不正是留守妇女们最害怕,最无奈的一个真实写照吗?大部分留守妇女承担着农村大部分的农活,同时也忍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虽然结了婚,虽然男人也很健康地活着,可是一整年却只能盼望着一次鹊桥相会,俨然是牛郎织女,家里没有一丝成熟男人的气息,夜晚只有与孤独寂寞相伴,听虫蛙鸟鸣解闷,平时不敢和别的男人搭讪说话,而基于妇女的特性,很多的话想说出来,又不能和老人说,更不会和小孩子说,有代沟。于是经常只能自己和自己说。"有时候想想真快要憋出病来!"赵艳芬翻飞着手里的织针棒飞快地说道:"最怕的就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农忙时节还好点,累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如果不忙的时候躺在床上有时候会睡不觉,感觉黑夜和寂寞就象要把我吞了去一样!有时候会特别害怕黑夜的来临。"赵春兰干脆放下手中织着的毛衣站了起来,看上去,她是四个妇女中身体体质最差的,脸色有点灰白,瘦瘦的,声音也有点干涩地说道:"我最怕的就是自己生病,平时丈夫不在家,遇到困难都是一个人摸索,一个人慢慢干,如果生病了,只能扛着,一是怕费钱,二是怕误了农活,一回家就蒙头大睡,有时候就好了。经常会感到孤独寂寞,尤其是在累了、闲了、缺钱的时候,感觉更强烈。家里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扛着,没敢告诉他,怕他在外面惦记,做不好活路"。
"我就是农村的,能在城里生活一辈子?打工不就是为挣点钱么?让他挣去好了,我还得呆在这里。一直打工,老了不能打工了怎么办?还有,城里人看不起我们打工的,想做个小买卖也不容易,城管也严,不敢乱摆摊,去租个门面转让费动不动就几万十多万的,有哪个钱我还做什么生意?而且这费那费的也交不起。"刘红一边说一边奶着自己不到一岁的孩子:"可是打心眼里我也真怕,怕什么?我这样呆在农村,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外面干出什么对不起我娘仨的事情来,你看小孩子才这么大点,如果他离开我们去找别的女人,我们娘仨怎么办呢?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担心,刚出去打工那两年,家里穷,他也没那个闲钱去做那些事,外面花花世界虽然诱人,可我还不担心点"刘军丽眼神中充满着担忧,也显露出她的极度不自信:"可现在不同了,他做起了包工头,手头宽裕了,听说在外面还和别的女人有染了,这些我都算了,因为孩子,因为这个家,我都受了,可是我真害怕那天他把那个女人带回来,我真害怕他从此离开我们娘两个,我真想去和他在一起,可是家里有老人,我又是独女,四个老人都是快70的老人了,得有人照顾啊!"说起这些,刘军丽眼中就贮满了泪水。"这都是命,只怪自己命不好!我天天给观音菩萨烧香,希望菩萨保佑我,希望菩萨点醒他不要受那个狐狸精的诱惑!"刘军丽补充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不准我和他一起去打工,我们只有一个女孩,他一直想要一个男孩,可后来我一直没有怀上,我去看过医生,医生都检查过了,我应该还能生育,没有问题,让他去检查,他不肯去,至少不愿意和我去,现在孩子读三年级了,可是一年见不到他几次,小时候甚至一看到他就哭,因为认不得他,觉得陌生和害怕,现在好点了。陈小红不自信的眼神里好象还有一层象雾一样的迷茫,因为劳累,刚刚三十的她看上去就象快40岁的人了。"我最怕的还是他和我离婚"陈小红坦率地说。
3,她们是家园的守望者,却是爱情的被抛弃者,是农村社会的弱势群体,往往也是被非法侵害者。
身累心更累恐怕是留守妇女们最伤心的事情了。走访中大部分妇女感叹最怕的就是受到侵害、诽谤和恶意中伤。
"现在世道开放多了,外出打工的也多了,但是土地得有人种啊,老人得有人养啊,小孩子得人带啊,更何况这是个家啊,得有个人支撑啊,于是留守妇女就越来越多,留守妇女其实就是个火药桶,闷了一二十年了,现在在不断地迸发中,甚至已经开始局部爆发了,农村离婚率上升,强奸案件频发,云南镇雄一村民长期霸占村里10余名妇女就是一个集中爆发的事例"在乡里做妇女工作的赵庆凤同志这样对笔者说。
三十优岁的蒋丽华面容清丽,神情清淡,一副超然脱俗的样子,但额角不经意间爬上的皱纹说明她是一个总是把烦恼和忧愁放在内心里面的人,虽然年近不惑,声音却仍然清亮如小莺般说道:"如果有机会,如果不是母亲病重,打死我也不一个人呆在这里,我宁愿和他一起外面去打工,怎么累,怎么苦我都不怕,流言如刀,杀人不见血啊!"
"我每天一入夜就带着孩子睡觉,有时候连电视都不敢看,"陈小妹一边说一边指着进房门的背后"你看,我的门都有三道门闩,第一道是原来就有的,第二道是我后来要他买了从里面锁的门闩,还有这个木棒,我把它从里面顶上去,现在农村治安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有牵牛盗马的现象,我们男人又不在家,只有自己死守着,可是晚上外面如果有什么动静,我们也是不敢开门的,不怕别的,就怕被诽谤"笔者触目处,是一个被门闩顶起的一个大大的凹陷。好象记录着陈小妹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
坐回到椅子上,陈小妹妹平静了一会,"象我这样,还算好的,好呆有个囫囵名声,能睡个囫囵觉,最惨的是我们村的陈东菊,嫁给我们村的黄金胜,这黄金胜平时文文静静的,说得上我们村里的大才子,可是外出打了两年工,留下孤儿寡母的,陈东菊身体弱,又多病,家里没有劳动力,一到农忙,她家请的工自然就多些,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我们现在是留守女人是非多啊,村里不由就传出陈东菊与有苟合的流言了,这黄金胜不知道是那个筋错了位,居然也起了疑心,回来又打又骂的,后来不是咋个整的,陈东菊就疯了,现在动不动就脱衣服,说"看,我是干净的,呵呵。。。。"好可怜啊!"
现年40岁的冯玉娥嫁给水城县蟠龙乡张老三时只有22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龄,也有着花一样的容颜。张老三是村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后来做起了小老板,冯玉娥开始觉得终生有了依靠,谁知道好景不长,张老三在广东重新找了个女人,然后就扬言要和她离婚。"我这个年纪了,不能企望再嫁人,我也舍不得两孩子,又不能带着两个孩子去娘家,我没有和他正式离婚,我没有在上面签字,我不是为了他,他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我是为了两个孩子!"
和冯玉娥一样命运的还有冯玉珍,是她本家的堂妹妹。冯玉珍的父亲是村里的支部书记,一个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支部书记,在村里声誉极好,待人和善,为人谨慎,当我们说起冯玉珍的丈夫赵雄飞时他却忍不住激动起来"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打小家里穷,父母也死得早,我看他有颗恒心的筋,做事也踏实,没少支援他,读大学我也支援了他一万元,后来连我女儿也嫁给了他,他一个穷学生,毕业又没有分配工作,谁愿意嫁他啊?!"冯支书显然由于一说起这事情就非常气愤,脸胀得红红得,眉毛有点上翘,待停了片刻,他还是又激动地开了口"狗日的,结婚后头两年,隔三差五地一年能回来几趟,给我们买很多东西,给孩子买衣服,现在大的娃近四岁了,小的也有两岁了,有一年多没有回来了,听说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好上了,还说要和我姑娘离婚,我糊涂啊,怎么就找上这么个白眼狼啊?"
4天各一方,后顾有忧 她们渴望夫妻团聚,家庭团圆,她们最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读好书,而孩子却往往因为缺少父爱威严而变得无法管教,还有公公婆婆的唠叨,这些都是她们的困惑。
赵小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大的孩子明年就要考高中了,小的读七年级,赵小花丈夫在外面算搞得比较活的一个,家里搞得也比较好,红砖水泥顶的三层小楼,少说也有200个平方,但是"总感觉心里头空落落的,好象少了什么又好象正失去什么一样,"小花这样对我们说:"最老火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我没读过多少书,希望孩子多读点书,不要象我们这样没出息,可是偏偏孩子们成绩不太好,大孩子考不考得上高中都难说,可我一说他,他回我"书都没读过,你懂什么?"我要说的话就被咽了回去,小孩子也不听话,孩子们大了,一个妇道人家管不好他们的,要是他们父亲在就要好点,压得住他们,我最怕的是:我们这样一辈子辛苦地努力,省吃俭用为了让他们读书将来有出息,可到头到却反因为没人管他们,教育他们,最后一事无成,甚至变坏,那才是我们一辈子都后悔的啊"话里透露出一种无奈的困惑。
和小花一样有着困惑的还有林金凤,林金凤只有一个孩子,读九年级,个子高高大大的。"就是不听话,经常和别人打架,有一次头还被打了一个大窟窿,在医院躺了近三个月。我不敢管他的,一说他,他还对我凶。"林金凤说"这全是他爷爷奶奶惯的,小时候我一打他,他爷爷和奶奶就站出来撑他,不准我打,也不准我骂,后来我一打他,他就跑到他爷爷奶奶房间里去!我只有自个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我是真怕没人管他,以后坏得没底儿!"
"一个人呆在家里,关键是缺乏理解,没个说话的,因为是两辈人,和公婆有代沟,没多少共同语言,我穿花俏点他们都要说,和别的男人说两句话,他们便如临大敌一样,其它方面也有很多处不来的地方。"还刚刚嫁入两年的杨金花说:"但是没办法,也只能将就着他们了,唉,想和他一起出去,他不准,说要我在家照顾老人,孩子才一岁,给老人带也不放心。"
笔者是一位计划生育工作者,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特殊性,与农村接触颇多,下车伊始,触目处,全是妇女,老人,孩子,偶尔听人家长里短,亦是谁家男人挣多少钱了,出什么事了,诸如此类,于是笔者便留了心,把一些交谈,采访,调查资料整理起来(基于相关人员要求,所有人物均为化名),本次整理基本反映的都是农村留守妇女生活艰难,无奈,辛酸,屈辱的一面,之所以这样写,亦是想引起大家对留守妇女这块特殊人群的注意,因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构建和谐家庭。而"留守妇女"在特殊的时期已经逐渐演变成"家庭的守护者","留守妇女"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其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家庭,亦会演变到社会,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和完美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们不但要从产生留守的中国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户籍制、不发达的土地流转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民工子女入学就业等相关制度入手,更要从留守妇女的身、心两方面对其进行关注、关爱。用制度的形式保障这个弱势群体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才能真正推进新农村建设更加和谐和完美。整个社会也才会更加和谐和完美。